- 所以你这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嫁给爸爸
- 所以你这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嫁给爸爸
- 屌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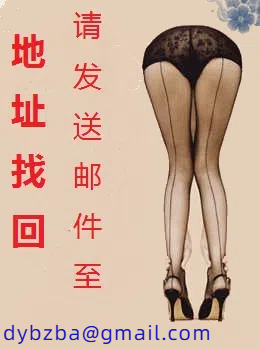
- 安卡希雅得了老年痴呆!?
- 安卡希雅得了老年痴呆!?
- 屌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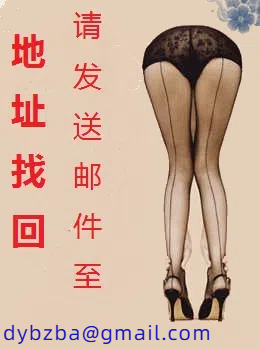
- 圣使少女无色纯钻的淫堕
- 圣使少女无色纯钻的淫堕
- 屌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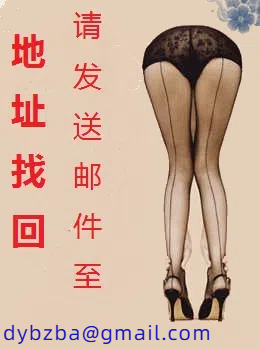
怕找不到回家的路!请截图保存本站发布地址:www.dybzwz.com
亲的声音。
很快,卧室里传来一声吮吸——没有停止,而是延续下来。
有多久呢,我也说不好。
恍若站在三千米赛道上,哪怕从小到大跑了几百次,对什么时候冲过终点线我还是没有把握。
当然,一切都有尽 。
。
后来吮吸声就停止了——起开,母亲说:恶心不恶心,林林在呢你老提儿子 嘛,来吧来吧父亲似乎急不可耐,有点让
嘛,来吧来吧父亲似乎急不可耐,有点让 哭笑不得。
哭笑不得。
药吃没之后母亲或许冷哼了一声,或许没有,总之床上的弹簧轻轻叫了起来。
吃啥吃,大夫说了心理 障碍父亲喘息粗重。
障碍父亲喘息粗重。
行了你,低沉 绷:一
绷:一 酒味弹簧还在叫,却被无限拉长,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。
酒味弹簧还在叫,却被无限拉长,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。
没准有个一分钟,就我寻思着是否该离去时,叫声戛然而止。
接着咚地一声巨响,只剩父亲的喘息。
妈个 他说。
他说。
此时,我已习惯客厅里的黑暗。
真是太怪了。
事实上,缥缈的天光透过窗户淌进来,整个天地都在盈盈而动。
然而,世界是沉寂的。
********************南街老面馆就在老南街,从平海法院骑车过去大概七八分钟。
迫于大太阳的 威,我骑得飞快,于是树影便在白昼中纷纷闪避,
威,我骑得飞快,于是树影便在白昼中纷纷闪避, 碎得如同老巷子里已在悄悄褪去的墙皮。
碎得如同老巷子里已在悄悄褪去的墙皮。
远远地,母亲坐在面馆门 的皂荚树下,见我过来便微笑着招了招手。
的皂荚树下,见我过来便微笑着招了招手。
她白帽黑裙, 顶的浅蓝色丝带在正午的风中轻轻舞动。
顶的浅蓝色丝带在正午的风中轻轻舞动。
一同舞动的还有葱郁间密密麻麻的青涩皂荚——平海皂荚树并不多,而这棵又格外粗壮,直冲云霄不说,几乎占据了多半条巷子,可以说每看到一次我都要忍不住惊讶一次。
就锁车的当 ,不经意地抬眼一瞥,我猛然发现枣红木桌的对面还坐着一个
,不经意地抬眼一瞥,我猛然发现枣红木桌的对面还坐着一个 。
。
白衬衫西装裤褐色凉皮鞋,大背 一丝不苟油光可鉴。
一丝不苟油光可鉴。
他在冲我笑,甚至学母亲那样向我招了招手——正是梁致远。
此 比皂荚树更令我惊讶。
比皂荚树更令我惊讶。
事实上我有点发懵,这货不 柴烈火地跟老贺撮合着,又跑平海
柴烈火地跟老贺撮合着,又跑平海 啥来了?还认得我吧?他站起来,笑呵呵的,嗓音磁
啥来了?还认得我吧?他站起来,笑呵呵的,嗓音磁 依旧。
依旧。
这不废话嘛,所以我说:那当然,梁总原本我想加个好,又觉得这么说太过场面宏大,只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